2019年04月23日16:57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擊: 次

左為王軍,右為羅馬克
10月27日下午,北京外國語大學意大利語教授王軍帶著譯作《瘋狂的羅蘭》來到思南讀書會第266期的現場,與意大利學者羅馬克(Marco Lovisetto)共同探討翻譯在重寫文本時的忠實與背叛、回歸與超越。
瘋狂的羅蘭:一棵巨大的千年古樹
人文主義是指導文藝復興發展的主流哲學思想,“愛情至上”是人文主義者最重要的追求之一。王軍認為,《瘋狂的羅蘭》雖然以宗教戰爭為背景,卻處處展現出贊美愛情、追求塵世快樂。他以史詩第1歌第1節的詩句為例,“我歌頌兒女情、美人、騎士……”,這句詩明確表示了作品主題,男女之間的情愛被置于首位。在王軍看來,“男女之間的情愛是對自然規律之間的尊崇,是人類情感和肉體的需要,是不可否認的自然本能。”
《瘋狂的羅蘭》熱情地歌頌人文主義者對大千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與冒險精神。王軍描繪道:“詩歌把許多驚心動魄的傳奇巧妙地串聯在一起,血肉橫飛的戰場,東方光怪陸離的城市……作品中還可以見到如法師、神君、巫女等魔法元素。”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試圖運用自主意識解釋自身和大自然,面對仍然無法解釋的事物時,他們不再愿意認為這是天意的安排,因而引入奇幻的魔法元素來詮釋未知。王軍提出,對魔法的追求預示了以觀察事物為前提,以實驗為基礎的現代科學的誕生,“若無人們對神奇器物的幻想,何來現代的機械制造?”
《瘋狂的羅蘭》以中世紀騎士傳奇為內容,但在作品中卻能隱隱看到近現代社會的影子。王軍介紹說,詩歌展示的本應該是奔馳在陸地上的戰馬和騎士的形象,然而阿里奧斯托卻采用大量的篇幅描寫航海場面,把“羅盤”“海圖”等專業詞匯嵌入詩中。“大量地描寫航海,說明已經進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近現代航海時代,體現作者對人的偉大發現很感興趣。”

王軍
詩歌還采用了一種極具現代感的例題式敘事手法。王軍談到,“許多動人故事交織在一起,相互拉動、相互影響,就好像一顆巨大的千年古樹,主干上分出了若干條枝干,宗教戰爭、羅蘭等騎士對安杰麗佳的愛和追逐,這些形成了非常巨大而又復雜的樹冠。”每當一個故事發展到關鍵的時候,如人物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致使讀者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的時候,詩人總會突然停筆,隨后轉換話題,開始講述其他的故事。間隔數歌,重新講這個故事。王軍說,“這種處理方法成為詩人手里一支魔棒,一方面詩人可以利用它避免自己的情感過于陷入其中,置身于故事之外能更好地操縱故事,使復雜的史詩內容更加合理地發展。”
盡量少地背叛原文
翻譯《瘋狂的羅蘭》無疑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譯者要面對的,不僅是顯而易見但無窮無盡的語言表達差異,更有意大利文學和中國文學在文體上的巨大鴻溝。王軍坦言,相較于小說,詩歌的翻譯更為艱難。一來是因為詩歌的內容比小說更濃縮,語言更具有概括性。二則是因為詩歌對藝術形式具有嚴格的要求,由此詩歌譯文也必須具有相應的藝術形式。遵照原著的詩體形式,王軍采用高難度的詩體翻譯這部意大利文學作品。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翻譯就是背叛,譯者的努力,只是為了盡量少地背叛原文。而用詩體翻譯《瘋狂的羅蘭》背叛得較輕,不是對原文形式的徹底背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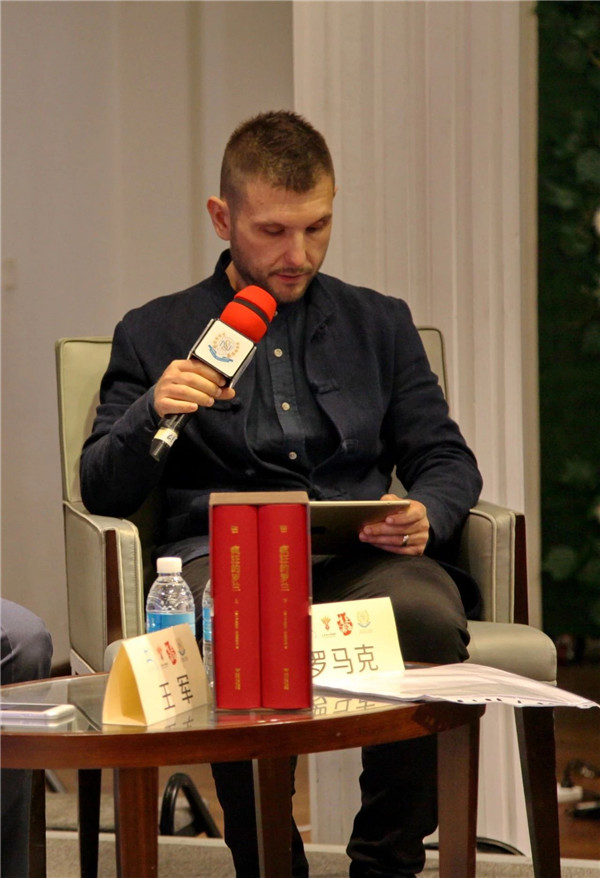
羅馬克
在選定了用詩體翻譯《瘋狂的羅蘭》后,王軍接著思考選定的格律“既要能被我國讀者欣然接受,又盡可能少背叛原文藝術形式”。在經過對傳統詩歌三言、五言、七言以及其他藝術形式的綜合考量后,王軍最終選定了中國戲曲常用的十字句唱詞的形式,在他看來,“戲劇唱詞是中國文學中唯一一種長篇韻律敘事文學形式,它與西方的史詩具有相似的敘事功能,再則十字句唱詞一般采用3+3+4的節奏,這種節奏也與意大利詩歌11音節的詩句相近。”
翻譯是一種重新詮釋
羅馬克提出,翻譯不僅是狹義的從一種語言到另外一種語言,而是廣義上的重新詮釋。“你從聽到一個文本,到頭腦中的解讀,都可以放到翻譯的理論內。時空性、文本互文性、社會政治性、理想讀者、文本功能這五個元素構成了翻譯理論的框架。”
在羅馬克看來,從文藝復興到現代社會,從西方到東方,王軍對《瘋狂的羅蘭》的翻譯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對比卡爾維諾于1970年用現代意大利語重寫的版本,“卡爾維諾的轉寫體現的是嚴謹的現實主義,像是一個機器精準的契合運作,同樣也有著某種輕盈,王軍的轉寫則更接近原文。”羅馬克也看到了王軍和卡爾維諾不同譯者間的共性,“兩個人都是在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交織網絡上做文章,通過復雜的交織來引人入勝,讓讀者能一直被吸引著。”羅馬克認為,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有各自獨特的世界觀,在廣義的重寫作品中,每一位譯者都能保持個體性,并且讓讀者能看見他們背后所蘊藏的世界觀,這便是譯者的可見性。
羅馬克提出,阿里奧斯托的《瘋狂的羅蘭》表現的是他對已經陷入危機的騎士精神和騎士世界的思考,而卡爾維諾的轉寫呈現的是對現代社會的思考,并且同時與阿里奧斯托的作品進行呼應。在阿里奧斯托筆下,雖然是宮廷精神和騎士精神衰落的時代,但仍然敘述查理大帝以及麾下的騎士征戰愛情、征戰的主題。當卡爾維諾處于現代的理性社會,考慮到現代讀者普遍缺乏耐心,他選擇抽離出復雜的人物關系,進行簡化敘事。羅馬克指出,每一個人物與作者有一定的關聯,“簡化后的人物不再作為一個個獨立的個體,而是同一個個體不同的反射,這樣最終都指向作者本身。”這樣的理念也應和著羅馬克的翻譯觀,即 “重新敘述即翻譯,翻譯即背叛”。

現場讀者
思南讀書會NO.266
現場:王若虛
撰稿:關 玥
攝影:杜湘濤
編輯:江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