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1日15:36 來源:思南讀書會 作者:思南讀書會 點(diǎn)擊: 次

從左至右為哥舒璽思、馬蘇菲、林恪、朱嘉雯
9月26日晚,三位荷蘭翻譯家、漢學(xué)家哥舒璽思、馬蘇菲、林恪攜《紅樓夢》荷蘭語首部全譯本做客思南讀書會第472期,與讀者分享跨文化翻譯中的挑戰(zhàn)與收獲。青年作家朱嘉雯擔(dān)任主持。
三位翻譯家歷經(jīng)13年努力,合作翻譯完成《紅樓夢》荷蘭語全譯本(120回),并于2021年11月在荷蘭正式出版。活動伊始,他們分享了與《紅樓夢》相遇、結(jié)緣到選擇合作完成翻譯的故事。

哥舒璽思
哥舒璽思的《紅樓夢》閱讀史是在翻譯學(xué)習(xí)與語言研究中不斷推進(jìn)的,在和語言學(xué)通史的合作中,她關(guān)注到《紅樓夢》中大量的特殊用語習(xí)慣,如“笑將起來”“好生”,由此開始了對文本的深度研究。馬蘇菲則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有著濃厚的興趣,在北大交流期間,她將偶然間相遇的《紅樓夢》帶回了荷蘭。林恪對《紅樓夢》的關(guān)注則循著自我學(xué)術(shù)志向的引領(lǐng),韓少功是他博士期間的研究對象,在韓少功的訪談中,他將中國文學(xué)的傳統(tǒng)追溯到了古典小說,引發(fā)了林恪研讀《紅樓夢》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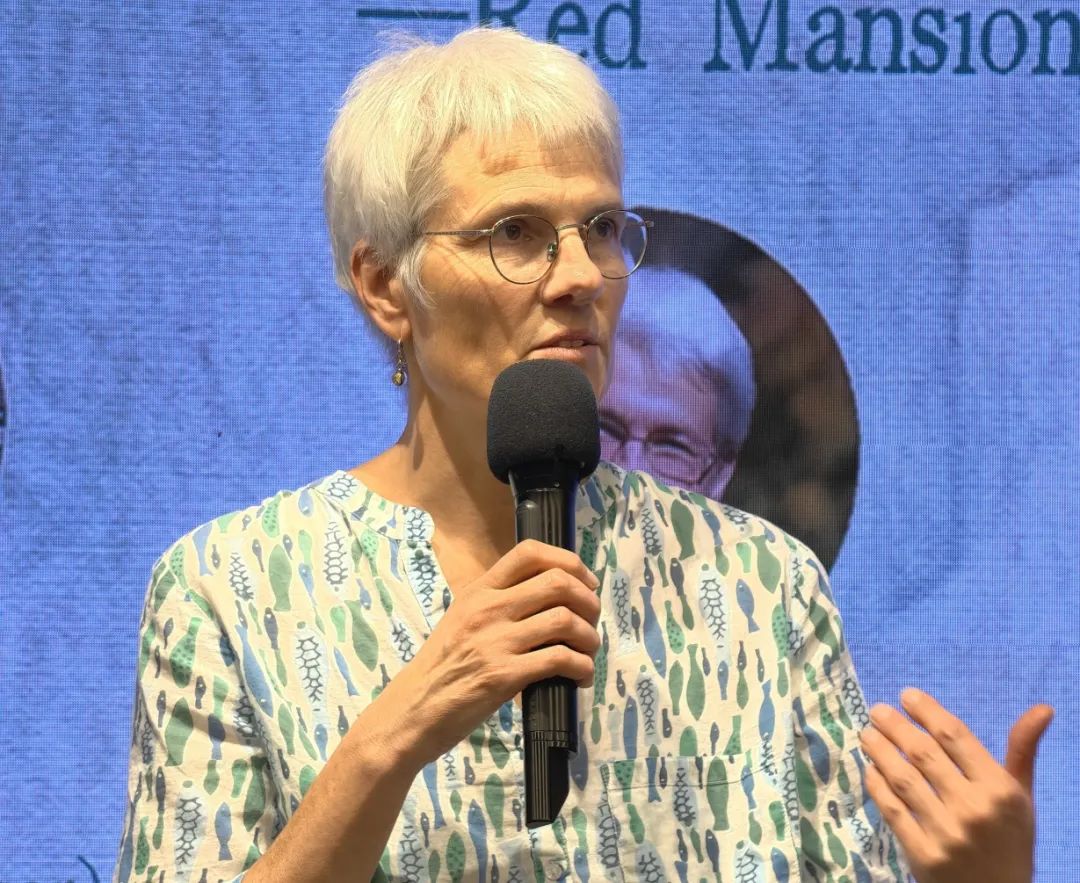
馬蘇菲
哥舒璽思諳熟中國的歷史社會,而馬蘇菲與林恪則分別專攻詩歌與小說的翻譯,在相異而又相交的學(xué)術(shù)研究背景中,三位翻譯家能夠各自發(fā)揮專長,在“環(huán)形流通的運(yùn)動過程”中,完成了《紅樓夢》的翻譯。“我們將這本浩繁的大書分成一個個小單位,每個章節(jié)都經(jīng)歷了傳遞、評論和回饋的流程。每六七節(jié)會進(jìn)行一次傳遞,大家會共同探討翻譯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再交給下一個人工作。”林恪說。

林恪
自譯本出版以來,《紅樓夢》在荷蘭重印兩版,銷售量達(dá)到了4000本,這與譯者們對理想讀者的設(shè)定息息相關(guān)。馬蘇菲談到,荷蘭讀者群體中,有著大量具有跨文化興趣的文學(xué)愛好者。“我們并不是為了學(xué)術(shù)目標(biāo)來翻譯這本書的,我們就是想翻譯給荷蘭市場的大眾讀者。通過這本書,他們能夠?qū)@個遙遠(yuǎn)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

朱嘉雯
林恪坦言,在翻譯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生活文化上的差異,如何在異質(zhì)的文化觀念中,盡可能減少荷蘭讀者的理解困難,是翻譯的題中之義。
除了保留了主要角色名和中國特有文化意象的音譯,三位譯者更多采用了意譯的方法,以接近本土讀者的生活習(xí)慣和語言表達(dá)。得益于一本《紅樓夢》植物詞典的幫助,他們找到了一些《紅樓夢》中的植物在荷蘭文化里的對應(yīng)物。又如翻譯中對“笑”的處理,譯者會將原文中統(tǒng)一的“笑道”翻譯成不同的笑,來適應(yīng)具體語境。

現(xiàn)場讀者
談及《紅樓夢》中的詩歌翻譯,林恪認(rèn)為,詩歌用典背后負(fù)載的文化和歷史是值得高度關(guān)注的。譯者需要“從文化淵源中重新挑選和保留最精華的東西,并用這些最精華的東西來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然而,在此過程中還是會有很多東西被犧牲掉,畢竟翻譯總是存在取舍的問題。”

現(xiàn)場讀者
關(guān)于《紅樓夢》中的愛情書寫,朱嘉雯談到了歐麗娟的一種觀點(diǎn),歐麗娟認(rèn)為寶黛的愛情是一種禮教制度之下的升華,而不是對封建制度的反抗,這反映出了不同時(shí)代、不同話語情境下的闡釋變化。《紅樓夢》的荷蘭譯本更是一次異質(zhì)文化碰撞,對此,馬蘇菲與林恪不約而同地認(rèn)為,《紅樓夢》中存在著許多人性、情感共通的地方。例如尤三姐的愛情,可以理解成一種跨越任何文化差異界限的愛情,這也是可以令荷蘭讀者共情的愛情。還有不少荷蘭讀者談及,在讀到黛玉淚盡而逝的結(jié)局時(shí),流下了感動的淚水。

讀者提問
哥舒璽思與林恪都談到,荷蘭文化傳統(tǒng)中同樣擁有著許多現(xiàn)實(shí)主義表達(dá),因此,盡管對荷蘭讀者來說,《紅樓夢》中的封建秩序是陌生的,他們依然能夠?qū)@部作品保持一定的“文化敏感性”,理解作家的“社會關(guān)懷與社會自覺”。
思南讀書會No.472
現(xiàn)場:戚譯心
直播:莊清揚(yáng)
撰稿:王瑞琳
改稿:郭 瀏
攝影:遲 惠
編輯:鄒應(yīng)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