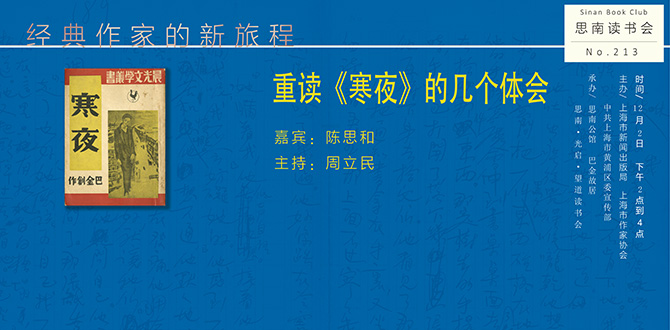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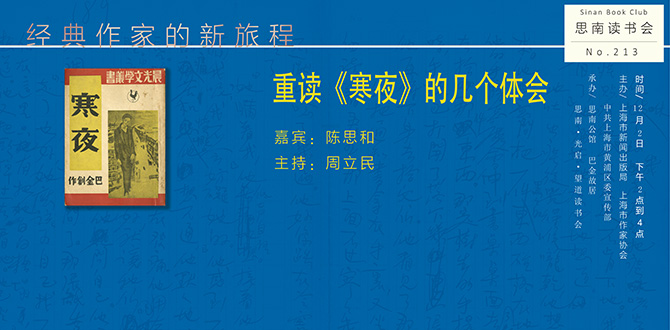
同構絕望與光明的復雜化敘事
陳思和向讀者率先提出了圍繞《寒夜》的兩處值得深入思考的邏輯。1944年巴金起筆《寒夜》的寫作,那一年巴金也正值與其戀愛八年的蕭珊結婚。現實幸福生活的映照下,巴金為何卻依然以絕望的筆法寫出了《寒夜》中家庭破碎、夫妻分離、甚至生離死別的故事?然而在早年被巴金定調于體現對個人前途、家庭社會的絕望的《寒夜》,在多年以后巴金自己重讀這部作品時又為何轉變了對《寒夜》的看法,認為:“充滿力量和光明”?對此,巴金自己沒有任何解釋。
陳思和把《寒夜》放回到了巴金的創作歷程中,為讀者們提供了一個縱向的解讀范式。陳思和認為,在巴金早期的文學創作中,作者的思想傾向很容易把握。例如巴金在《家》《春》《秋》中,塑造了善惡鮮明的三代人:封建大家長形象的高老太爺、好壞參半的父輩形象以及以“覺慧”“覺新”為代表的純真第三代人物。陳思和指出,在巴金創作的后期創作中,《憩園》《第四病室》和《寒夜》的主題則趨漸復雜,而《寒夜》最具復雜性。
《寒夜》中的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樹生本是自由戀愛為基礎建立的家庭,但由于婚后汪文宣的社會地位逐漸邊緣化和曾樹生渴望追求高層次的生活享受產生沖突,最終曾樹生選擇舍棄了孩子和丈夫離家出走,汪文宣在絕貧困交加中死亡。初讀后,讀者普遍都會對人生境地悲慘的汪文宣產生同情,但陳思和引導讀者們換位進行深度思考,理解“曾樹生離開汪文宣的合理性。” 巴金筆下被家庭困住腳步進而轉向追求個人自由的汪文宣,似乎也彰顯出了希望與光明的力量。陳思和結合巴金……【詳情】



